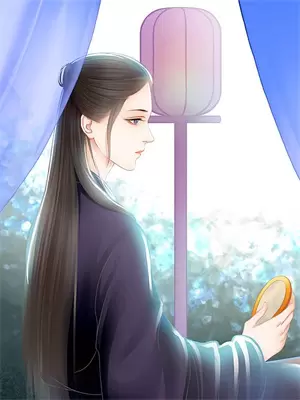
1 蓝衣惊魂我在相亲对象的书房里发现一张全家福。照片上每个人都穿着同款蓝色运动服,
笑容灿烂。唯独本该是女儿的位置,被人用黑色墨水粗暴地涂掉了。
他温柔解释:“那是我妹妹,去世很多年了。”当晚留宿他家,阁楼传来小女孩的哭声。
我摸上阁楼,发现门缝渗出同样的蓝布料纤维。门内指甲刮擦声突然停止,
一个童声轻轻问:“姐姐,是来陪我玩的吗?”陈默的声音在身后响起:“看来她很喜欢你。
”第二天去他诊室,撞见他正穿着照片里那件蓝色运动服。
电视新闻滚动播放:“第六名儿童失踪,监控拍到蓝色运动服身影…”他拉上窗帘,
转身微笑:“现在,该换你穿那件衣服了。”2 消毒水之谜陈默的书房,有一股味道。
不是书香,也不是男人惯有的烟草或古龙水味。是消毒水。浓烈、刺鼻,
带着医院走廊特有的冰冷气息,顽固地渗透进每一寸空气,
混合着旧书页散发出的、被时光捂得发闷的尘埃味。这味道,像一层无形的薄膜,
包裹着这个据说代表着学识与温雅的私密空间,也隐隐刺激着我的鼻腔。
介绍人说他是个抢手货,儿科医生,温文尔雅,手指修长干净,说话能安抚人心。
此刻他站在书桌旁,暖黄的台灯光晕柔和地勾勒着他线条分明的侧脸,
倒确实衬得起那些溢美之词。他递给我一杯温水,指尖不经意擦过我的手背,
带着恰到好处的体温和礼貌的克制。“随便看看。”他声音低沉悦耳,
像大提琴在寂静中滑过的尾音。我的目光有些无处安放,只好投向那占据了一整面墙的书架。
厚重的医学典籍,
光泽——《希氏内科学》、《尼尔森儿科学》、《格氏解剖图谱》……它们如同沉默的卫兵,
排列得一丝不苟,像他梳得纹丝不乱的头发,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秩序感。
视线漫无目的地扫过那些代表着人类身体奥秘与病痛挣扎的标题,最终,
被书架顶层一个极不起眼的角落,死死地攫住了。那里,一个蒙了层薄灰的相框,
像被遗忘的时光碎片,静静地杵在几本大部头的夹缝里。相框本身是新的,深色木质,
边缘被打磨得光滑圆润,透着一种刻意的、与内容格格不入的考究。但框住的那张照片,
却脆弱得令人心惊。它已经严重泛黄,边缘卷曲起毛,像被岁月反复揉搓过的枯叶。
照片上是一家五口,一对中年夫妇端坐在前排略显僵硬的藤椅上,身后站着三个半大的男孩。
他们无一例外,都穿着同一种款式、同一种蓝色的运动服。那蓝色,蓝得极其刺目,
像盛夏正午毫无遮挡的、能把人晒脱皮的天空,
又像是某种批量生产的、缺乏灵魂的制服标准色。照片里的人都在笑,
笑容被定格在那个遥远的瞬间,灿烂得近乎虚假,仿佛能穿透陈旧的相纸,
散发出当年灼热阳光的温度,却丝毫暖不了此刻看照片人的心。然而,那片虚假的欢乐,
被照片中央一个狰狞的“黑洞”硬生生撕裂了。
就在前排父母与后排儿子们之间的视觉中心点上,本该站着一个人的位置,
被一种极其粗暴的方式彻底抹去。不是裁剪,不是撕掉,而是用大量浓稠、肮脏的黑色墨水,
一遍又一遍,带着刻骨的恨意或是恐惧,狠狠地涂抹覆盖。墨水因为用力过猛而晕染开,
像污浊的血迹,侵占了旁边两个男孩运动服的衣角,
最终形成一个边缘毛糙、深不见底的黑色窟窿。那片纯粹的黑,
带着一种沉默的、令人窒息的暴力感,粗暴地挖走了画面的核心,
只留下一个吞噬一切的空洞。它突兀地杵在那里,像一张咧开的、无声尖叫的嘴,
又像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,让整个温馨的全家福瞬间弥漫出森然的寒意。我的指尖,
无意识地变得冰凉。“在看什么?”陈默温和的声音毫无征兆地在身侧响起,
近得我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更清晰的消毒水气味,混合着他自身一种洁净的、类似皂角的淡香。
我猛地回过神,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了一下,喉头发紧,干涩得几乎说不出话。
手指有些僵硬地指向那个刺目的黑洞:“那个……位置,原本是……”声音像砂纸摩擦。
陈默的目光随着我的手指落在那张全家福上。他脸上的笑容没有消失,甚至更柔和了些,
唇角微微上扬,眼底却沉淀下一种深沉的、近乎悲悯的怀念。他抬起手,修长干净的食指,
以一种极其轻柔、近乎爱抚的姿态,轻轻拂过冰凉的玻璃相框表面,指尖不偏不倚,
正落在那片狰狞的墨迹中央。那动作,小心翼翼,
像是在触碰一件价值连城却又脆弱不堪的珍宝。“哦,那里啊,”他叹息般开口,
声音压得更低,像大提琴最低沉的那根弦被轻轻拨动,“那是我妹妹。
很多年前……一场意外,她走了。”他顿了顿,目光似乎穿透了相框的玻璃,
投向某个遥不可及、只有他自己能看见的虚空,“年纪太小,父母太伤心,
后来看到照片就受不了,才涂掉的。留个念想,又怕睹物思人。”他的解释合情合理,
语气里带着恰到好处的、被时光沉淀过的沉重与一种近乎完美的克制。指尖的凉意,
却顺着血液,蛇一样蜿蜒着,一路蔓延到了心脏。
我看着他那双依旧温和、甚至称得上深邃好看的眼睛,试图在里面找到一丝伪装的裂痕,
一丝慌乱,或任何能印证我心头那莫名寒意的证据。可没有。
那双眼睛平静得像深秋午后无风的湖面,深不见底,波澜不惊。他的话是合理的,
父母痛失幼女,行为过激可以理解。但视觉不会骗人。那片浓黑的墨迹,
它带来的冲击太直接,太暴烈,像一块刚从冰窖里挖出来的石头,
沉甸甸地、带着透骨的寒气,狠狠砸在我的心口上,
瞬间驱散了之前对他建立起的所有基于表象的好感。留下的,
只有一种难以言喻的、冰冷黏腻的不安。晚餐的气氛变得微妙而滞重。
长条餐桌上铺着素雅的米白色桌布,精致的骨瓷餐具闪着冷光。陈默的餐桌礼仪无可挑剔,
话题也围绕着书籍、音乐和一些无关痛痒的社会见闻,试图营造轻松氛围。
我努力维持着表面的平静,回应着他的话,唇边也扯出得体的弧度,
但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、像被磁石吸引般,飘向书房虚掩的门缝。
那片浓稠的黑暗仿佛已经烙印在我的视网膜上,每一次眨眼,它都顽固地浮现出来。
那片墨黑,像有生命般,在记忆里蠕动。窗外,不知何时下起了雨。起初是淅淅沥沥的敲打,
如同细密的鼓点。渐渐地,雨声变得密集、沉重,豆大的雨点狠狠砸在玻璃窗上,
发出沉闷而持续的噼啪声,如同无数只手在急切地拍打着牢笼。
路灯昏黄的光晕透过湿淋淋的玻璃,在室内投下扭曲晃动的影子,
将房间切割成明暗交错的怪异空间。“雨太大了,”陈默放下银质的餐叉,
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,背对着我,看着外面被雨水冲刷得一片模糊、只剩下昏黄光团的世界。
雨水在玻璃上蜿蜒流淌,像一道道浑浊的泪痕。他的声音透过雨幕传来,
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、体贴的权威感,“开车不安全。这种天气,
高架桥和隧道口最容易出事。”他转过身,脸上是恰到好处的关切,
目光温和地笼罩着我:“客房是现成的,很干净,我母亲偶尔会来小住。留下吧,安全第一。
”他的提议无懈可击。窗外恶劣到极致的天气成了最有力的挽留理由,
堵住了任何推辞的借口。我张了张嘴,喉咙里却像塞了一团浸水的棉花。然而,
内心深处那片被墨汁涂黑的疑影,非但没有被雨声冲淡,反而像汲取了水分的藤蔓,
疯狂地缠绕上来,无声地、却又无比强硬地阻止了我想要立刻逃离的脚步。那股寒意,
源自书房的寒意,此刻似乎正顺着地板缝隙丝丝缕缕地渗出来,缠绕着我的脚踝。
我最终只是点了点头,喉咙里艰难地挤出干涩的一个字:“好。”3 阁楼童声深夜,
万籁俱寂。窗外的雨势似乎小了些,从狂暴的冲刷变成了绵密低沉的呜咽。
但一种更深的、属于子夜的、带着坟墓般湿冷气息的死寂,彻底笼罩了这座空旷的房子。
陌生的床铺,陌生的气味消毒水和陈旧的木头,还有心底疯狂滋长的恐惧,
让我的神经如同被拉到极限的弓弦,每一寸都绷得紧紧的,无法放松一丝一毫。
老旧木质结构的房子在温差和湿气的双重作用下,偶尔会发出一两声轻微的“咯吱”呻吟,
每一次细微的声响,都像冰冷的针尖,精准地刺在我紧绷的神经末梢,让我的心跳骤然失序。
就在意识被疲惫和紧张拉扯着,即将沉入混沌深渊的边缘时——一个声音,
穿透了厚重的死寂和雨水的低泣,清晰地钻入了我的耳朵。
呜……呜……像被什么东西死死捂住嘴巴后,
从喉咙深处拼命挤压出来的、极力压抑着的哭泣。细细的,断断续续,
带着孩子特有的、未变声的稚嫩腔调,却又浸透了无边无际的恐惧和令人心碎的绝望。
它并非来自隔壁房间,也不是楼下客厅。声音的来源,
清晰无误地来自上方——来自那个被楼梯尽头浓重黑暗彻底吞噬的、从未被提起过的阁楼!
血液瞬间冲上头顶,又在下一秒冻结成冰。我猛地从床上弹坐起来,
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擂动,每一次搏动都沉重地撞击着肋骨,发出擂鼓般的闷响。
手脚一片冰凉,指尖控制不住地颤抖。那哭声时隐时现,像一根冰冷的、带着倒钩的丝线,
缠绕着我的神经,越收越紧,几乎要勒进骨头缝里。纯粹的恐惧像冰冷的潮水,
瞬间漫过了我的脚踝、膝盖,向上蔓延。
那片被刻意涂抹的黑暗所激起的、令人窒息的好奇与深入骨髓的不安——却像一只无形的手,
推着我,动作僵硬地掀开了被子。双脚踩在冰冷刺骨的地板上,寒气瞬间从脚心直冲头顶。
客房门被我无声地拉开一条缝隙。走廊里一片漆黑,伸手不见五指。
只有尽头安全出口指示牌那一点微弱的、如同鬼火般的幽绿光芒,
在地板上投下模糊而扭曲的影子,更添几分阴森。那细细的哭声,在走廊的寂静中,
似乎变得更加清晰了,像冰冷的钩子,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牵引着我。我赤着脚,
像幽灵一样滑出房门,踩在冰冷光滑的地砖上,每一步都小心翼翼,屏住呼吸,
全身的感官都调动到极致,生怕发出一点微响,惊动这死寂中蛰伏的未知怪物。通往阁楼的,
是一段狭窄得仅容一人通过、陡峭得近乎垂直的木楼梯,
隐匿在走廊尽头一个不起眼的、被阴影完全吞没的拐角。楼梯口没有门,
只有一片浓得化不开、仿佛能吸收一切光线的黑暗,像一个无声张开、择人而噬的喉咙。
那股熟悉的消毒水味,在这里似乎更加浓烈了,浓得呛人,它霸道地压过了一切其他气味,
混杂着一股难以言喻的、类似陈旧灰尘和潮湿木头腐烂混合在一起的、令人作呕的腐朽气息。
我扶着粗糙冰冷的墙壁,指甲无意识地抠进木纹的缝隙里,一级一级,
几乎是手脚并用地向上挪动。越靠近阁楼,那股混合的怪味就越发浓郁,
冰冷粘稠的空气几乎令人窒息。阁楼那扇低矮、破旧的木门终于出现在眼前。门板斑驳,
布满深浅不一的划痕和污渍,门缝紧闭,透不出一丝一毫的光亮。哭声,就在这扇门后面!
那么近,近得仿佛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木板。细弱,无助,带着穿透骨髓、冻结血液的寒意,
丝丝缕缕地渗透出来,钻进我的耳朵,缠绕住我的心脏。恐惧像冰水灌顶,
但那股被激发到极致的、近乎自毁的好奇心却驱使着我。我伸出手,
指尖因为极度的寒冷和紧张而剧烈地颤抖着,一点点,
一点点地靠近那扇冰冷、仿佛散发着不祥气息的木门。就在距离门板仅仅几厘米的地方,
我的动作,猛地僵住了。全身的血液似乎在这一刻凝固。门缝底部,极其细微地,
嵌着几缕纤维。在安全出口指示牌那点幽绿、如同鬼火般微光的映照下,那几缕纤维,
呈现出一种无比熟悉的、刺目的、让我瞬间头皮炸开的蓝色!和那张诡异全家福照片上,
所有人穿着的运动服,一模一样的蓝!它们像是被强行从门内刮擦、拖拽出来,又或者,
是里面某个穿着这种布料的人,在挣扎、在抓挠门板时,无意间被粗糙的木刺勾落下来的。
我的指尖,完全不受控制地、鬼使神差地,轻轻捻起其中一缕。触感粗糙,
带着一种廉价工业布料特有的、毫无温度的冰冷。这触感,像电流一样窜遍全身。
就在我的指尖捻住那缕冰冷蓝色纤维的瞬间——门内,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