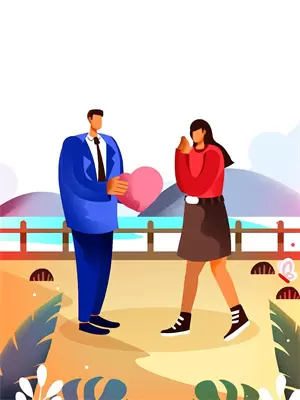
我才迟钝的察觉到似乎秋天又来了。
和庄从文在一起的第十年,我确诊了胃癌。
我抬眼看向天空,眼睛一阵酸涩。
为了乐队巡回演出多日未归家的庄从文,手机一向是勿扰状态。
我看着手机里的对话框,最后一次交流可以追溯到上个月,剩下的都是我在自说自话,分享日常。
手指将文字删删减减,最后还是一切清零。
我将皱巴巴的诊断书胡乱塞进包里,打车回了家。
门口是早已融化的草莓蛋糕和干枯的玫瑰,上面的署名是—生日快乐,永远爱你的从文。
我露出一抹苦笑,多日的期盼就这样破碎。
将我的生日错记,送我过敏的草莓蛋糕,枯萎的玫瑰惹来蝇虫在空中盘旋。
最后,二十七岁功成名就的他伪装成十七岁,假装依然爱我。
我在门口呆站了很久,大脑发怔。
直到潮湿的暖意传来,我伸手摸了摸鼻子。
不知不觉,泪水混合着殷红的鼻血蔓延开来。
我拿过一旁廉价的卷纸,搓成一团堵住鼻孔,流出的血很快就将纸巾浸湿。
那年我和庄从文还住在阴冷昏暗的出租屋,为了追求他的梦想,将所有的钱买下昂贵的架子鼓,在隔壁租了个鼓房。
后来甚至连日用品都无力承担,为了节省开支趁促销买了十几箱廉价的卷纸,一擦嘴一层薄薄的纸屑就黏在嘴上,我们还笑得不可开支。
我变得习惯性购买卷纸,生怕又回到那段蚊虫鼠咬的时光。
如今,只得到庄从文淡淡的嫌弃:你的眼光怎么变得这么廉价?我仰着头,一只手颤抖的拨出一个号码。
对面接的很快,我有些受宠若惊,小心翼翼的问出积压已久的话。
从文,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?对不起呀,我是不是吵到你了。
我今天又流鼻血了,医生说是我太上火啦。
我好想你,你什么时候回家呀.....最后一句,我快要泣不成声,身体的不适和情绪的脆弱让我不顾一切的想见到他。
电话那头只有均匀的呼吸声,许久,对面传来一个温柔的女声:他睡了,林灵。
我的心如坠冰窖。
张了张嘴,却干涩的说不出话。
林灵,还有....生日快乐。
男朋友的小三搂着我的男朋友,祝我生日快乐。
我的鼻血一滴滴落在地上。











